第144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整理 | 实习记者 李雨桐
前几日我读到一篇题为《多少年轻人,在给苹果手表做“牛马”?》的报道,文章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苹果手表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帮助人们摆脱手机的控制,通过运动等方式获得身心放松。但如今,它成了不少年轻人‘折磨’自己的‘新型刑具’。
很多人调侃自己说,一旦戴上了智能手表,就像‘上了套的驴’,不干出点成绩来不肯停下;又像主动戴上‘电子镣铐’的‘运动囚徒’,不把卡路里消耗的数字刷到新高,就不能‘出狱’。”
报道中提及,苹果手表有一个运动闭环功能——手表将监测佩戴者当日活动消耗卡路里、锻炼时间和站立时间,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健身需求设定属于自己的目标,完成目标,三个圆环才能合上——让许多用户患上了“合环强迫症”。
这篇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月初刚刚开始使用苹果手表,目前正处于与这只电子表的“蜜月期”。作为一个使用苹果手表还不满一个月的新用户,我发现苹果手表确实在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上施展了重要的影响力;但我也发现,苹果手表在进一步将社交网络填入我的生活缝隙,争夺我的注意力。
01 苹果手表的悖论:健康监测的好帮手还是另一种手机的延伸?
林子人:这块手表很快改变了我佩戴手表的习惯。以前虽然我每天都会戴手表,但只会在出门的时候戴,一回到家立刻摘掉。但是自从有了苹果手表以后,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收集我的身体数据,除了晚上洗澡的时候,我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戴手表,因为这样它能够监测我的睡眠质量。手表的震动是非常有效的闹钟,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在我的手腕上震动一下,就立刻把我唤醒。
苹果手表收集的身体数据也的确对我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我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地按时睡觉,尽量保证8小时的睡眠目标。这个月我也基本做到了隔天蹬一次动感单车,看到三个圆环合上的特效确实挺有激励效果的。当然,我现在给自己设定的运动目标还比较基础,但对我而言,先培养出定期运动的习惯是最重要的。整体而言,我对苹果手表的使用体验还是挺正面的。

尹清露:我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买的苹果手表。当时觉得最好用的就是睡眠的监测APP,因为它不仅可以监测睡眠的时长,还可以监测睡眠的深浅,就是到底有效休息了多长时间,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整个指标可能是红色的,睡得好就是绿色的,非常直观。我那段时间在写论文,作息不好,又非常焦虑,这个监测睡眠的功能还是挺有用的。我当时很喜欢在手机上摆弄一些项目管理或者to do list相关的软件,那个手表正好有类似的功能。你今天做的事情它会实时列在屏幕上面,非常简洁。
我后来放弃使用苹果手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要每天都要充电。但它不像手机那么刚需,有时候我就会忘记充电。其次,我逐渐发现那些之前我觉得能坚持下来的习惯,比如睡眠监测、项目管理,实际上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到最后,它最实用的功能就变成了在有人给我发微信的时候通过震动来提醒我,我可以随手抬起来看是谁给我发了微信。于我而言,苹果手表就变成了手机的一个过渡产品。
潘文捷:很多需要从体育课上了解的知识我其实是从手表上学到的,比如说关于睡眠结构,包括快速眼动期还有非快速眼动期,非快速眼动期包括深睡眠和浅睡眠这两种不同的睡眠状态。我还从手表中学到,人在进行深呼吸的时候,呼的时间是吸的两倍。
我的手表是一个华为基础版,不是很贵。目前为止它让我感到最有用的一个功能是通过蓝牙跟手机联动。有一次我出去玩的时候把手机丢了,通过这个功能,我很快就找到了手机。另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是计步功能。我现在很喜欢戴着它走路,因为每次计到一万步的时候它会给我放一个烟花的特效,让我很有成就感。
但这个手表也会带来一种“try to relax”的悖论。比如说我戴着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它要给我计算睡眠时间了,然后我就会暗示自己要努力睡着,但越努力越睡不着。咱们聊天室一般要聊一个小时,但它半小时就会提醒一次久坐,可我又没有办法站起来跟大家聊天,就感觉有点无奈。
董子琪:我买苹果手表还蛮早的,大概是在2016年。我买它的动机也不是监测健康什么的,只是想看起来更酷炫。那个时候很流行开着特斯拉带着苹果手表的科技新贵形象,我还亲眼看到过这么一个人,心里很羡慕他,想着我也要戴一块苹果手表。那时候虽然很穷,但分期付款也可以付得起,然后就买了。我连结婚的时候都戴着苹果手表,虽然手表跟婚纱完全不匹配,但我觉得可以显示出我是一个现代科技新贵,跟其他新娘不一样。我很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通过微信去滴别人,这个好像是其他客户端没有的。我用这个功能骚扰了很多朋友,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苹果手表。
不过后来我就把手表忘了,彻底地丢在家里某个角落。我觉得苹果手表的消费性质还挺明显的。当我想要去修它的时候,苹果店员会直接说你还不如再新买一个,因为修它的价格很高,也不确定能不能修好。我觉得人在某个阶段会对这东西特别感兴趣,但过了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把潮流丢掉。
02 人机合一的“赛博格”:“苹果生态”的诱惑与成瘾
林子人:总的来说子琪是一个挺厉害的消费者,在使用了那么多苹果设备之后还能脱离这个系统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个词叫“苹果生态”,它指的是苹果公司开发的从各种硬件、软件到服务这一系列的产品和技术的集合。不同苹果设备通过各种技术和服务实现了这个生态的连接,让用户能够在设备之间无缝体验。一旦成为了苹果的用户,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很自然地吸引你去购买新的产品,让你生活中一个新的部分融入到这个系统当中。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人们愿意购买和使用苹果手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开头提到的那一篇报道里,接受采访的大多都是苹果产品的重度用户,他们对于追求可视化的运动成就呈现出一种非常痴迷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外人看来甚至是难以理解的。比如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朋友们一起去唱K,突然所有人的手表都提醒他们站立时间到,然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家怎么看待苹果公司推出这个手表产品的初衷和它如今呈现出来的效果?这种合环强迫症背后的成瘾机制是怎么形成的?
虽然我使用苹果手表的时间没有特别长,但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它使用了一种游戏化的设计。除了合环,当你达成了一定的运动目标,它还会给你颁发徽章,来激发你的动力。游戏化的策略其实在很多产品设计里都有体现,只不过我觉得苹果公司格外擅长运用这一点。

徐鲁青:我没有用过苹果手表,但我觉得苹果系统就是会给人一种比较强的成瘾机制。我之前用的是安卓手机,换成苹果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离不开这个系统,很难再换回安卓了。苹果手机真的太简单了,简单到根本没有那么多文件处理的烦恼。安卓有一个类似文件收藏夹的功能,就是你上传一个文件到手机上,你大概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你也可以把它点开,看是不是要删除或者传送给别人,类似于一个手机的后台。但在苹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后台,一切都被非常简单和明显地推到用户面前,也没有那么多文件处理的烦恼,所以后来我完全不想用回安卓手机了。
我之前在澎湃思想市场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苹果系统的一种“闭源独裁性”:它会故意屏蔽掉用户在使用手机时背后那些繁琐的程序,连用户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设备里有什么文件以及它们的位置,这种屏蔽在给用户带来很好的使用体验的同时,也会让人比较少去思考背后的运转和操作逻辑。
林子人:我这两天在读法国学者赛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统治”的章节提出,用户彼此之间的互补吸引现在体现在少数具有强大吸引力的霸权信息技术设备上。我觉得像苹果系列产品其实就是一种霸权信息设备。
为什么说它是霸权?因为它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架构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要素来组织:第一是具有低可变性的中央组件,第二是具有高可变性互补组件,第三是中央组件和互补组件之间的模块管理接口。这种架构模式在确保基础稳健性的同时,还能够实现非常好的拓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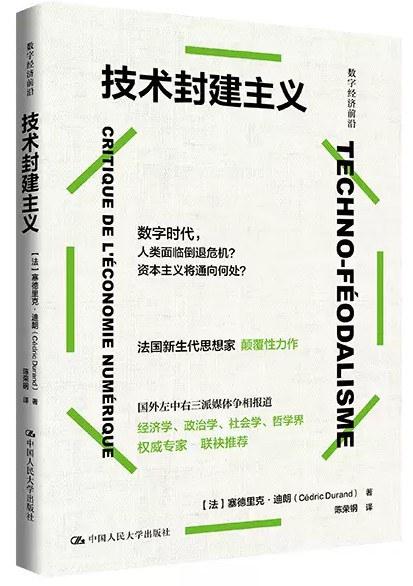
用户们可以在不同的模块之间自由地穿越,但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使用这些设备的方式,其实全部都是依托于一个统一平台之上,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用户是这些数据基础设施(比如说苹果生态)的“俘虏”。随着使用这些设备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这些设备上逐渐沉淀出了一组让用户与众不同的元素,包括用户的熟人网络、用户的浏览习惯、用户的搜索历史、用户的兴趣、用户的密码,甚至是用户的一些私人信息。因为永不断线,我们的人机融合也在越来越紧密。
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得特别有意思,
“为了让我们摆脱认知活动中最机械的事情,算法为我们每个角色提供了对我们共同优势的直接和持续的支持。随着这些干预持续增加,我们的生活与云端的联系就变得更加紧密。”
放到苹果手表这个案例里面,它所谓的“让我们摆脱认知活动中最机械的事情”,就可能是我们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想要计算我们的睡眠时间,它帮我们解决了这个事情。但这些东西反过来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干预,而且你一旦形成了这个习惯,就会发现很难摆脱。你会需要每天都定时佩戴它,才能持续不断地生成相关数据。我觉得如果要讨论苹果手表以及其他苹果产品成瘾原理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
尹清露:子人和鲁青提到的苹果霸权系统让我想到了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他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刚刚被引进国内。他认为技术应该是敞开的,或者应该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边缘”。大家可能都认为东京地铁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但其实里面存在非常多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说东京地铁准点的背后就是有很多力在共同作用的,当人流量或者其他因素发生变化时,这个准点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改变。这可能正好跟苹果系统所带来的东西是恰恰相反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尽力减少不稳定性,让用户意识不到技术的存在。

我觉得苹果手表设计的初衷跟现在所达到的效果可能是一致的,最开始宣传的就是它很轻巧,没有束缚。我之前读过一篇关于运动APP的文章,说这种终端装置讲究的是与身体的亲和,这种粘着跟渗透一方面是空间上的,一方面是时间上的。空间上指的是装置粘附在你的身体上,非常自然没有任何的异物感。时间上指的是可以为日常健身以及所有生活时间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记录和监测。
如果用“赛博格”来描述的话,我会觉得手机可能已经是算是一种“赛博格”,但它只是没有粘附在身体上,所以苹果手表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人机合一的“赛博格”。我发现很多科技博主也非常注重如何让技术融入生活,苹果手表的很多功能让我可以不用手机,一抬手就可以处理很多技术上或者是网上的事情。似乎手表变成了人的另外一个器官,我觉得这一点也许是可怕的。
03 算法和数据背后:看不见的隐私和自主性
林子人:当消费者全心全意沉浸在这种生态系统当中,主动去交付和自己有关的各种数据的时候,其实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技术封建主义》援引了学者肖珊娜·祖博夫的文章,她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些科技公司创造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目标就是通过预测和修改人类的行为来创造收入和控制市场。
在祖博夫看来,“监视资本主义”的公司正在建立一个“大他者”的基础设施,从人类的社会经验当中汲取无限的资源,包括我们的浏览数据,消费行为,运动数据等。当它收集到足够多的相关数据时,就会构成一个大数据。这些公司就可以利用大数据制定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影响用户的行动。
按照祖博夫的说法,这些公司对各种资源进行了重新安排,然后以行为指令的形式返还给我们,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我们的自主性。苹果这家公司也完全可以通过你的运动数据来做一些推荐或是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影响你的行为。从公司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潜在的盈利机会,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科技产品的消费者应该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董子琪:我比较害怕的是,这些数据收集似乎带有一种强制性,我没有主动要求,却不得不面对它们。一次我和一个科技公司团队开会,有一个team leader突然就站起来了,他说是他的苹果手表提醒他要站起来。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你的手表提醒你啊?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很享受、很珍视被一个器械所关爱、所重视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监视这件事情的负面意义小很多。
这个道理可以套用到另外一个事件,现在手表的应用场景之一是小天才电话手表,这个手表是大人给小朋友戴的,小朋友之间可以通过这个手表互相加好友,他们会用电话手表呼叫对方,形成一个新的社交圈,所以更多家长们会更倾向于去买这个手表。

这个手表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它可以为家长提供孩子心情状况的评估,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他是微笑、平常还是生气。通过数据统计,家长可以看到孩子一天的心情是如何的,这也是一种监视。昨天我坐地铁,旁边的妈妈突然打电话给她的小孩,说我看到你几分钟都没有动了,做题怎么做这么长时间?这说明这个妈妈一直在监视她的孩子,但这样的监视是有必要的吗?孩子会想要自己的心情每时每刻都被家长关注到吗?
林子人:我很怀疑,这些手表类产品真的能够测量出一个人的心情变化吗?其实苹果手表也是有这个功能的。比如说它会提醒你,你现在压力值爆表了。如果各位使用的是苹果手机,打开那个健康APP,里面有一个功能是让你描述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它会给你很多选项,让你选择出今天心情状态的原因,之后你就可以管理或者说是记录这一个月的心理状态。不过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和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是不是反而让我们不相信自己最真实的内在感受了?
徐鲁青:我觉得这种预设好像就是说焦虑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你要注意一下,不要那么焦虑。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法注意,就算我注意了,我还是很焦虑。
04 钟表的隐喻:身体如机械,健康靠个人
林子人:我觉得电子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使用“手表”来查看时间,也可以用它来查看自己的身体状态,这里面有一种很强的隐喻性。
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欧洲梦》,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观念其实都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是不断演化的。书中有一个章节讲述了激发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常常是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西方人对时间的认识是怎么变化的。书中提到了“时间的世俗化”这个概念:在中世纪的晚期和现代早期,教会和新出现的商人组织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时间的意义和本质的激烈斗争。教会认为时间是审慎的,而商人则认为时间是自己的,用来获利的。
现在我们知道,后者这种时间观取得了全面的胜利。15世纪晚期,巨大的钟楼就成为欧洲城市的常见景观,通常矗立在市政广场中心。最早的时钟是没有指针的,只会在整点敲钟;到了16世纪,时钟开始每隔15分钟报时;发展到后来,时钟开始拥有了指针,到了17世纪中期发明了钟摆;再后来出现了分针,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秒针。计时工具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小巧,越来越便携可带,直到出现了手表。

我们用手表看时间是为了让我们的行动和社会要求——比如说职场的要求——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协调个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机制。看时间可以说是一种“向外观看”的行为,而用手表来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只和自我有关的“向内观看”的行为,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身体内部运作是如何去回应时间的,电子表其实统合了向外观看和向内观看,把对自己身体的重视拔高到了和通过一定行为对他人、对外界产生影响一样高的权重。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哲学性,非常值得分析和思考。
徐鲁青:子人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有一次聊天室也讨论了时间变迁的话题。在最开始人类是通过自然来测量时间的,比如像太阳的运动、星辰或者潮汐。机械钟表发明之后,时间的测量才有了固定的标准。最开始对于日晷来说,一天不是24个小时,可能是25个小时或者23个小时,因为不同季节里一天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时间用机械钟表来测量运算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钟就被固定好了。机械怎么走,人就怎么走。当衡量主体产生了变化的时候,人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感知也产生了很大变化。
以前对于身体是什么样,更多是依托我们的切身感受。比如像我今天好像胃疼,好像睡得不够,更多说的是我自己感觉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现在把这种感觉寄托在电子手表上,或者是电子手表的数字上,类似我今天心率是什么样,我今天睡了多少个小时,我的睡眠程度是深还是浅?我觉得对于身体评估标准的转换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于身体的理解。我之前尝试去过健身房,健身教练给我用量表测了很多数据,告诉我我的身体有哪些问题,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像机械一样,被拆分成一个一个组件。
我失眠的时候就会跟着做冥想,感觉还挺有效果的。冥想是一种特别重呼吸的运动方式,我也会把我的感受投注在平时身体的呼吸上,对我来说,一呼一吸好像就变成了时间测量的方式。在那之后,我会把注意力从机械的时间开始慢慢转向呼吸的时间,比如说我做一个平板支撑的时候,往下往上,就感觉时间度量上发生了变化,好像不再受机械时间度量的束缚了。
尹清露:关于性情外化,我想到一个例子。最近韩国女团New Jeans的一首歌的MV有跟苹果的合作,所以MV里面要出现一些苹果的产品。MV女主角对一个男生心动了,她举起手,能看到苹果手表上显示出一个大大红心。在MV里,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所以那个手表也用了一个很漂亮的表带,后来很多人就为了买那个同款的表带去买了苹果手表。
潘文捷:用了这种手表之后,好像健康就只是自己的责任,每时每刻都要监视我自己,但其实健康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2005年,公共卫生医师迈克尔·马尔莫研究全球范围内过早死亡因素,谈到健康状况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梯度压力、早年的贫困、社会排斥、工作、失业、社会保障、成瘾、食物和交通。
其实,贫困与社会阶层跟疾病发生的联系是非常大的。《病患悖论:为什么“过度医疗”不利于你的健康?》一书谈到,有很多人现在很注重预防疾病,经常做各种筛查来找出自己得病的早期征兆。这些人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且做预筛的人大部分是社会地位更高的低风险人群。那些不觉得自己需要看病、不关注自己健康的人反而健康威胁更大。我就在想,我们这些用苹果手表来关注自己健康的人,跟那些更加需要健康关注的人是同一批人吗?他们可能其实更需要这个手表来关注自己的健康,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途径,或者完全没有想过怎样去监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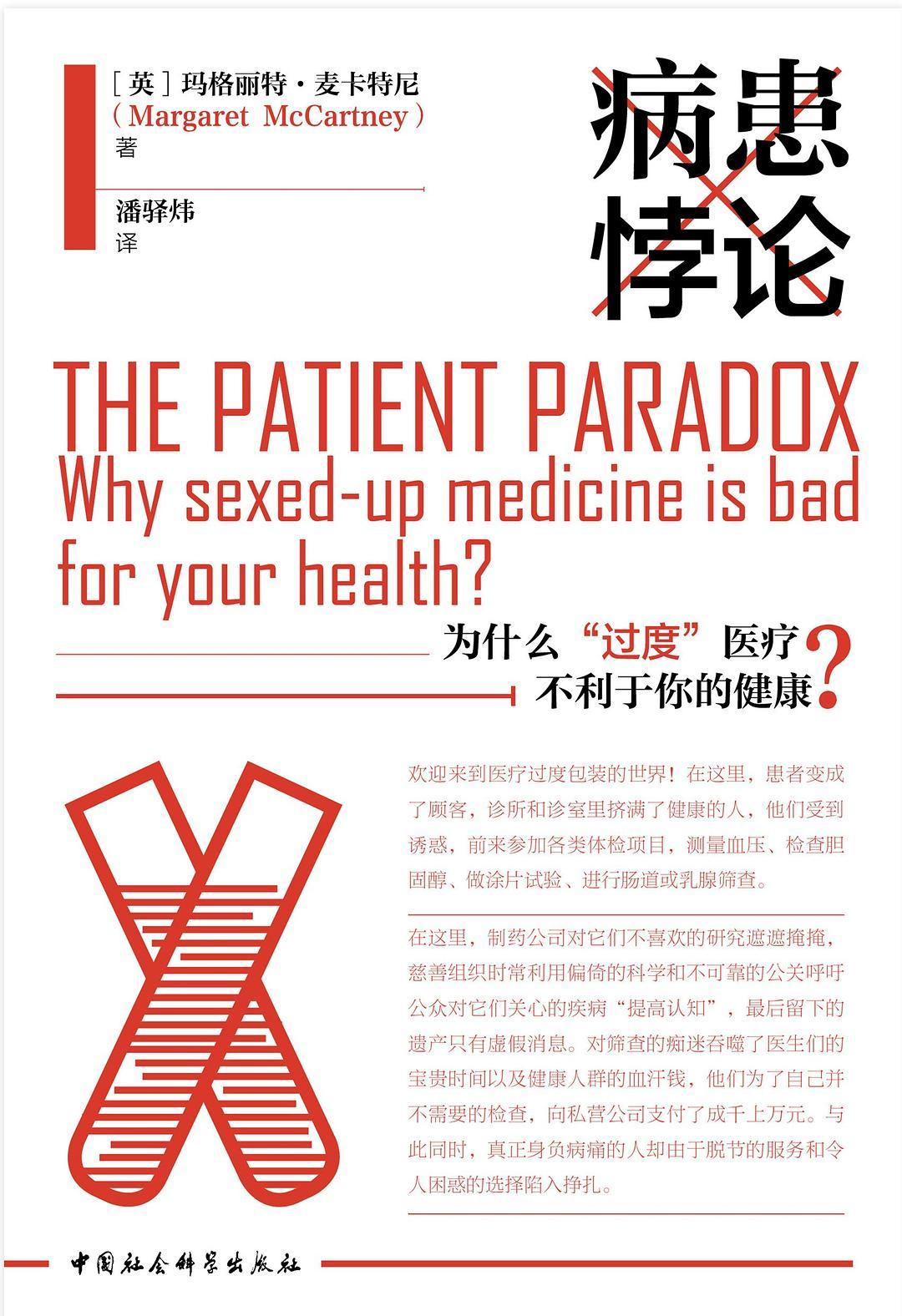
董子琪:但给山区儿童发手表这样的行为好像也不太对吧?
潘文捷:发手表感觉还是在一个自己关注自己健康的阶段,就好像把手表变成一个秘书,提醒你每天自己要喝水,每天自己要注重你的睡眠时间,但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公共卫生需要提供的。
林子人:如果说苹果手表的使用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的话,我觉得它体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当下的社会心态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需要每天、每时、每刻监测自己的身体数据,去尽全面地、客观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并且做出相应的回应。我觉得这些是这类运动手表产品给人们的潜台词。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8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8号